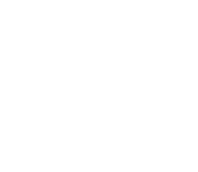田黎明的画和人之间,有一种天然而明确的对应性。他的画是漂浮的雾气,我透过雾气看到田黎明。
可生长的创新
艺术创新,是1978年以来中国文艺界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曾经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天天都在冥思苦想怎样创新,但是少有人把创新本身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认真探讨。近年来有各种各样的创新。有的创新当时很轰动,后来就没有了,就像孩子们在沙滩上努力垒起来的城堡和房子。还有一些创新,或许当时没有那么轰动,却像银河系里的恒星,持续地发出光亮。创新是有类型性的。田黎明的创新,有一定的引领性和恒定性。因此,田黎明和他的画,对当代中国画创作的影响,也具有一种渗透性。这在大量的创新型画家中为数不多。因为历史的选择,是很严格、很严酷、没有什么客气和温情的。
田黎明的创新,带来了什么呢?
阳光、空气、水,是田黎明绘画表现的主体。三者共同的特征,就是从容、透明、轻盈、恬淡、静谧。田黎明画那些在田野、在河边、在山林里,只是自然随意地站着、倚着、躺着,几乎没有任何戏剧性动作,梳着两条长辫子、穿着一身过去农村女孩的朴素衣衫,双眸淡淡地看着世界没有任何刻意表情的少女;还有那些似乎只知道在村边小河里无拘无束游泳而不知道人间愁苦的孩子。他们本身就像阳光一样明朗,空气一样透明,河水一样清澈。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一点被世俗功利熏染后的污浊。那些不甚清晰有点飘忽,离今天很远而且越来越远的关于童年、田野、少女的记忆,经过想象和艺术的加工、提纯,变成了宣纸上的梦和诗。可以肯定,那些纯真的少女曾经深刻地映入过他儿时的眼帘和心灵,而那些在河里快乐戏水的童子,他,就是他们中的一个。

图为田黎明作品《2001高原阳光》,208.6×123.6厘米。
正是这些,构成了田黎明中国画作品中非常特殊的抒情性和诗意,并适应了时代精神的另一种需要——这个时代的情绪太喧嚣太躁动,色彩也太强烈太斑驳,田黎明给这个时代带来了精神上一些非常缺乏而全新的东西,以及对美好、宁静、诗意、纯真的期待。画中流淌的那股清纯得几乎没有一丝杂念、杂质的情愫,就像清晨被露水洗过的嫩草叶子,像山涧边初开的一朵不知名的小花。这是影响他一生的记忆积淀,也是他画里最让人感动的东西。

图为田黎明作品《2014窗外》,282.6×149.2厘米。
田黎明的创新,从上世纪80年代到今天,一直都在坚持、努力地行进中。创新要有恒久性。其奥秘就在于,创新的图式语言本身要有可生长性,要像一颗有生命活力的种子,能在时间的流动里长出新苗、树干、树枝、绿叶,能够年复一年地开花、结果。田黎明作品的图式语言便具有生长性。他1988年创作的《小溪》《草原》,背景一片空无,年轻和年长的女性面容和身躯极其朦胧,依稀可辨。慢慢地,他笔下的人物五官轮廓变得稍稍清晰起来,景物也从一片空无里淡淡地浮现出来。田黎明最早画古装人物与现代女性、儿童,后来从女性扩展到男性,从儿童扩展到成人。他作品的图式结构也由无背景、单个人的简单,慢慢变成了人物和景色的有机交集、人物和人物参差组合的复杂,便有了《群贤毕至 俯仰天地》浑然一体的结构。他的创作视野由早期的淳朴农村慢慢走向现代城市,穿着时尚的都市女性、扫街的农民工、提着行李的打工妹纷纷闯入他的画面。在那里,富有原生态的大地、河流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高高的楼群和如织的车流、人流。这样,他的绘画不但有抒情性,也有了颇具抒情意味的社会性。艺术语言的生长是一个缓慢漫长的过程。田黎明绘画语言的生长过程清晰、有序,每一步都走得很坚实。
“淡”的发现
中国画用墨,常规上既不焦也不淡,超过常规的那些墨色都是附加性的,不能成为主体,比如极淡的淡墨和焦黑得发涩的焦墨。田黎明把这些非常规性的原来只是局部或偶尔使用的绘画语素,发掘出来并加以持续放大,进而摸索成一套能持续使用的规范的绘画语法系统,使之潜在的功能得以释放。极淡的淡墨和同样极淡的淡彩浑然一体,让中国画拥有了一种全新的审美上的陌生感。
中国画历来强调笔墨。20世纪以来,中国画对墨的发现和运用,超过了对笔、对线的发现和运用。人们发现不常使用的淡墨、宿墨、焦墨,都可以成为中国画墨色的主体、主调。淡墨和焦墨处于中国画墨色的两极。墨色的核心是对水的分寸感的掌控,水是中国画技术体系中最不直接露面但操纵一切的精灵。如果说焦墨是用水的极度收敛,那么淡墨就是用水的极度放纵,放纵大量的水对墨的极度稀释。在田黎明的作品里,极淡的淡墨使画面基调呈现抒情意味极浓、带有梦幻色彩的淡淡的银灰调子,给人余音袅袅的想象和韵味。
我把田黎明的艺术语言的创新,称之为“淡”的发现。他有一张山水高士图,画题即为《万物皆淡》。画中两个淡如疏影的高士,面容衣着淡如羽翳,站在淡如晓雾的山石间,流露出一派万物与我何干的淡泊心情。对于田黎明来说,“淡”是一种艺术的整体。不仅是墨,还有色。
田黎明绘画对色的新的发现,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外各种各样的绘画流派大规模地被引入中国有关。在新的艺术语境下,中国画的发展呈现一种新的趋势,就是对色彩和新颜料大规模地运用和开掘。这种开掘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画的表现手段,使传统中国画焕发出新的时代气息。但这种开掘和运用,经常还是集中在常规意义上的。田黎明的用色,可以看到印象派注重外光的明显影响。那些飘落在人物脸庞和躯干上的光斑,是他对印象派外光的理解和消化。更重要的是,田黎明的用色有自己的巧妙用心。和他的淡墨一样,九分水一分色,色溶于水,极淡极淡,淡到大地、山川、林木、庄稼和人物的色彩,都有了一种离纸而去的漂浮感和轻盈感,把中国宣纸吸水、化水的特点用到了极致。这是一种境界。应该说他对色彩的运用,是非常规的。以水色、水墨渲染形成的水汽迷蒙的块面,构成田黎明绘画的主体。人物和景物徘徊在平面和立体之间,再加上他用色的纯净,就有了一种视觉上似是而非的朦胧诗意,有了一种心理上宁静纯澈的安详稳定感。
我总觉得田黎明的画,某种意义上有点像20世纪80年代初的朦胧诗,飘忽、朦胧。但是,朦胧诗指向晦涩,总是要人注解,否则很容易产生歧义。在当年,关于朦胧诗产生了很大的争论。而田黎明的画,好像并没有引起很大的争论。因为他的朦胧指向了清晰、清新——形象物象是大体清晰的,情绪主题是清新的。我看他的画,就像自己走在早晨的田野里,有雾气扑面而来,低下头就可以看见草丛中露珠的感觉。田黎明描写的是心理上属于“清晨大地的东西”。他对极淡色调的发现和运用,完成了对美的追求。

图为田黎明作品《2020红》,纸本水墨,70×40厘米。
(作者为文艺评论家;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化室主任,上海艺术研究所所长,上海市艺术创作中心主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上海市第十一届政协常委,上海市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主任、研究员;评论作品曾获第五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一等奖。本文为新时代美术高峰课题组、中国画“两创”课题组专稿)
(《人民周刊》2024年第23期)
(责编:汪翠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