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4年是常书鸿诞辰120周年、李承仙诞辰100周年,他们的儿子、著名画家常嘉煌在本刊开设专栏“嘉煌说敦煌”,回顾常氏家族的文化苦旅。
在敦煌,自古就有致敬先驱、守护遗产、铭记先辈、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一代代学者踏沙而行,弘扬优良的传统,赓续古老的文明。20世纪30年代,在常书鸿等人的推动下,“敦煌学”应运而生。1996年,李承仙、常嘉煌母子继承常书鸿遗愿,在甘肃党河开凿现代石窟,完成了延续敦煌文明的又一伟大创举。
我出生在敦煌莫高窟一所元代寺院中,从小听到的是隔壁喇嘛的诵经声和远处传来的大佛殿檐角铁马叮咚声、小溪流水声和树叶哗哗声。
父亲说,这叫鬼拍掌,新疆大叶杨的树干有很多像眼睛一样的结疤,一起风叶子就哗哗作响。
成年后每次回家,眼前都是游人如织的纷繁景象。一天清晨,清风沙沙作响,当第一缕阳光照射进莫高窟大佛殿时,眼前突然展现出父亲在自传《九十春秋》里描述他初到莫高窟的场景:“不远处,透过白杨枝梢,无数开凿在峭壁上的石窟,像蜂房一样密密麻麻。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烁夺目。整个画面,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翠的锦绣展现在我们面前,令人惊心动魄……”于是,我创作了《莫高窟大佛殿清风》。

几十年来,我追寻这种玄妙的感觉,在浙江音乐学院进行音乐绘画研究,与壁画里的云气、飞天飘带、乐器的融合产生了新的构思,并创作一系列作品。
青山一道同风雨,明月何曾是两乡?2023年12月18日,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发生6.2级地震,余震不断,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倡议日本甘肃同乡会向灾区积极捐款捐物,并于震后72小时内将第一笔捐款汇入统战部账号。2024年新年伊始,日本爆发地震、海啸,火山喷发,灾难接踵而来,我也收到来自国内各方的关怀。
悠悠世路,乱离多阻。艺术是治愈心灵创伤的良药,敦煌是苦难与美好共存的艺术,这里有延续千年的文化脉络、穿过大漠的风沙雨雪、历经岁月的荒芜与时间的洪流。不同肤色的人们和合共生,不同地域的文明和谐交融,古老的石窟熠熠生辉、生生不息,成为超越时空的精神栖息地,成为举世瞩目的艺术宝库。开凿于1996年的敦煌党河石窟,将承启古代千年敦煌石窟群的艺术,留给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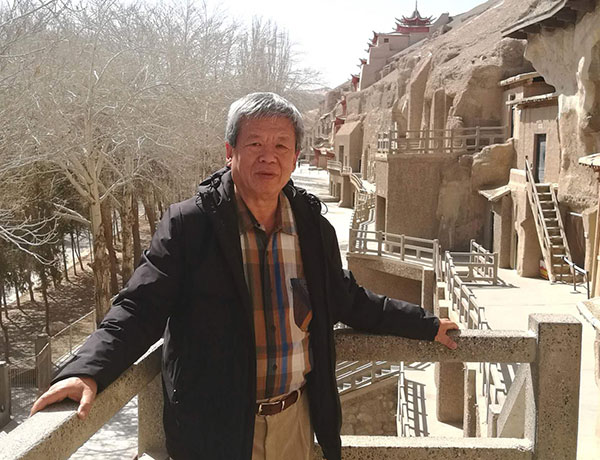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我的父亲、母亲选择坚守敦煌,用画笔对抗苦难,以文艺涵养精神,扎根西北荒凉之地,永葆艺术热忱,厚植爱国情怀。
2024年,是我父亲常书鸿诞辰120周年、母亲李承仙诞辰100周年,我将用自己的感受叙述我的敦煌记忆,缅怀双亲思故人。
阅读链接
1935年秋,巴黎塞纳河畔,旧书摊上一部名为《敦煌石窟图录》的画册,震撼了在法国声名鹊起的画家常书鸿。他下定决心——回国!寻访敦煌!
1943年2月20日,古丝路上响起新驼铃,常书鸿踏上河西走廊。历时月余抵达敦煌,千年荣辱就在眼前:400多个洞窟、2000多身彩塑和约4.5万平方米的壁画,积淀着千余年的灿烂艺术,遭遇数次洗劫后,壁画被火熏得漆黑、洞窟坍塌、栈道被毁……
“从看到它的第一眼起我就在心里说:哪怕以后为它死在这里,也值!”敦煌等来了常书鸿,残破的洞窟,等来了涅槃的火种。
1943年3月24日,敦煌莫高窟的中寺前,新挂了一块木牌,上书: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
彼时的大西北,充满荒凉、贫穷、灾难和死亡。时局多艰,经费短缺。向国民政府要钱,一无所获。常书鸿借用民间的智慧与力量为莫高窟筑墙,用一把小刀在墙上刻下:“敦煌百姓,功不可没。”
1945年,抗战胜利。常书鸿噙满热泪,站在大佛殿上,抱着那根巨大的钟槌,用力撞响了那口大铁钟。他怎么也没料到,和抗战胜利的消息一起到来的,还有当时教育部的一纸电文:“抗战结束,百废待兴,国家重建,资金有限,从即日起,撤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心爱的学生、相濡以沫的同事、曾经同甘共苦的挚友……一个个都走了,家都支离破碎了,“哪怕只剩下我一个人,也不会离开敦煌!不会离开莫高窟!”常书鸿对着千佛洞说。
荣辱盛衰几千年,雄鸡一唱天下白。1949年9月28日,塞外晴空如洗,阳光灿烂,一面鲜艳的红旗飘扬在敦煌古城城头。人民创造的艺术宝库,终于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几年后,常书鸿赴京筹备敦煌文物展览。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对莫高窟人的第一次检阅。展览引起了中外参观者的极大热情和关注,给敦煌带来了巨大的荣誉。《人民日报》刊发报道《艰苦工作八年的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人员》,便是对全体同志的表彰。
(本文节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敦煌守护人》)
(《人民周刊》2024年第1期)
(责编:张若涵)

 010-65363526
010-65363526 rmzk001@163.com
rmzk001@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