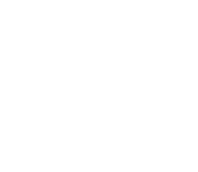艺术创作没有约束就没有自由
艺术创作者必须充分自由才能创作出优秀作品,绝不能受任何约束。这是一说。但又有一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玉不琢,不成器”,即是在最讲自由的国家强调个人充分享受自由,但仍要有严格法律的约束,而且越是讲究自由的国家,法律的约束越严。反之,没有约束,也就没有自由,艺术创作亦然。
一位外国评论家说:“艺术发展于约束,在自由中灭亡。”这话颇有道理。
常见的一个比喻,火车必须在铁轨上(约束),才能自由奔跑。
艺术家创作时,个人必须自由,但创作中必须遵守某种约束,自古皆然。从原始社会到汉代,艺术处于不自觉状态,但艺术创作仍有一定约束,比如“存形莫善于画”,画必须有形,画鱼就得像鱼,画鸟就得像鸟。若毫无约束,胡涂乱抹,画什么不像什么,在那个时候,画就无人承认,也无人保存。
东晋顾恺之的“传神论”标志着艺术进入自觉时代。顾恺之以“传神”与否评价一幅画的优劣,画必须传神,这就是约束。南齐谢赫总结“六法”,画必须受“六法”的约束:必须有气韵、生动;必须有骨法,讲究用笔;必须应物,即象形;必须随类赋彩;必须讲究构图;必须有传统的功力。北宋郭若虚称:“六法精论,万古不移。”
天才艺术家可以冲破约束,但必须建立新的约束,比如“随类赋彩”,若不用彩,用水墨,则必须受“墨分五彩”的约束。“墨分五彩”即使是自己的发明,也必须自我约束。游戏尚有规则,何况艺术?规则就是约束。
文学艺术有了功力常感处处自由
文学艺术和做人一样,做人要自由,但必须有约束,越自由,就越要有约束,大自由必须有大约束。
所有的人,在约束中成才、成长,在放任自由中毁灭。世界上没有无约束而绝对自由的人和事。
格律诗是世界上最完美的诗,艺术水平最高。约束越严格的,形式也越完美。中国的格律诗约束最严,平仄、押韵、对仗,必须严格遵守,还有不能犯孤平,不能“合掌”,甚至不能邻韵通押,等等。若不严格遵守约束,就不被人承认是格律诗。
约束严,只要功力到了,这种严格的约束反而会得到另外一种自由,犹如铁轨限制火车轮,却使火车飞奔得更快更畅。熟悉格律诗的人都知道,格律的规定会使自己的艺术有意外的飞跃,关键在于有无功力。没有功力,一动笔就不自由;有了功力,处处自由。
艺术也如此,画人物画,缺乏造型能力,怎么画?若有了中国传统的造型能力,只能画传统的人物画,像陈洪绶、任伯年这样的大家也只能以线条勾出人物的外轮廓而已。因为他们缺少西方解剖的功力。到了徐悲鸿及其后的画家,便可以自由地画出人物形体的内在肌肉、骨骼的结构,因为他们学过西方的解剖学,知道肌肉、骨骼的生长规律。所以他们便可画出肌肉的内在变化在外表的体现。若没有这种功力,就没有这个自由,也就永远受这个约束。
画山水画、花鸟画,必须有画山水和花鸟画的基本功;要创新,就更需要基本功和新的思想。否则,将一筹莫展。
抽象艺术出现于西方,西方画以色彩美著称,搞抽象艺术,必须具有色彩美(对比中呈现的美)的基本功,否则抽象画也不能成立。中国画是以线条美著称的,搞纯抽象画,就需要更强的基本功,而不是自由地胡涂乱抹。
有些“艺术”仅仅是艺术史家作品而已
到了现代派,有一部分艺术家,完全没有艺术创作的基本功,创作没有任何约束,绝对自由,不要色彩,不要线条,不要造型。比如法国的克莱因,1958年举办过一个展览,展厅内无画、无雕塑,空无一物,据说:“因为空空如也,所以力量无穷。”他又从窗口跳下去,也是艺术。达·芬奇的画,放在那儿,记载不记载,都是存在的,像克莱因这些“艺术作品”,如果没有美术史家的文字记载,就根本不存在。艺术到这个地步,就真的灭亡了。
观念艺术,重在观念;行为艺术,重在行为;装置艺术,重在装置;艺术已退居其次了。
杜尚的小便池,如果没有艺术史家的记载,仍然是小便池,自行车架仍然是自行车架,“波普”中那些垃圾仍然是垃圾。这些之所以能成为“艺术”,其实是艺术史家文字记载的结果。它是艺术史家的作品,而不是“艺术家”的作品。像克莱因的“艺术作品”连垃圾也没有,完全是艺术史家的文字。实际上,克莱因完全没有受过任何绘画艺术的训练,他只作过爵士乐的演奏员,是毫无绘画基本功的。
有人说,人人都是艺术家,吃饭、走路、穿衣都是艺术,没有约束,绝对自由。“人人都是艺术家”,实际上人人都不是艺术家。正如一个国家如果所有的人都是国王,实际上人人都不是国王。
在各种绝对自由的“艺术”和“理论”影响下,于是有人在木框上蒙一层白布,一笔不画;有人在白布上戳了一刀;有人在白布上贴几张报纸;有人拿出一个橡胶皮……都号称艺术。十几年前,有几个欧美“艺术家”跑到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找来一些南京的艺术家,合作一幅大画,他们把巨幅宣纸和西洋画接在一起,铺在大草坪上,有人朝上面泼墨汁、泼水、洒广告色、撒土、扔石块、贴报纸、插树叶……宣称这是中西艺术家共同创作的超越世纪的艺术,应该名载世界艺术史中。他们“创作”时,也有路过的人看看,都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于是把我找去,说这是盖世艺术。我只好去看。只见一片垃圾,我问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回答是:“意思全在画中,绘画只能用绘画回答,不能用语言。”我说:“我看不懂。”回答是:“你看不懂,我们也看不懂,就像鸟叫,你也听不懂,鸟也不懂……”“我们不受中西任何艺术语言的约束,完全是我们独创的语言。”“你是杰出的艺术史家,应该记载和研究我们这种独创的艺术,才能名扬世界。”我没有记载也没有研究,他们开始十分宝贝这幅“杰作”,但无人收购、无人拍照,也无地方收藏,痛惜很久,大骂史家无知,最后只好扔到垃圾堆了。得到的只是打扫垃圾工人的骂声。
但有一点,我研究了,参加合作的中国的“艺术家”全是基本功极差的人。基本功好的艺术家没有一个参加。
至于“鸟叫,无人听得懂”,典出毕加索回答一个女人的质问。而实际上毕加索的每一幅画都有意义,都能讲出很深的道理,像《格尔尼卡》,能写出很长的论文去论说其中的每一个细节,并不是“你不懂,我也不懂”。
其实“独创”最为容易,用屁股蘸墨汁,朝宣纸上一坐,用自行车蘸墨汁在宣纸上骑过,都是史无前例的“艺术”。把乳罩戴在膝盖上,把安全套套在头上,都是史无前例的行为艺术……
艺术到了这个地步,也就灭亡了。
如前所述,游戏尚有规则,艺术岂能没有规则?有规则就必须受规则的约束,艺术在约束中才能发展,不受规则的约束,完全放任自由,将导致艺术必然灭亡。
(本文为新时代美术高峰课题组、中国画“两创”课题组专稿)
(《人民周刊》2024年第22期)
(责编:汪翠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