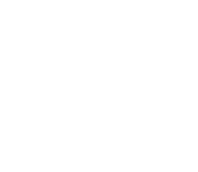伴随着20世纪通俗大众艺术的兴起和独盛,中国精英艺术失落了。精英艺术乃至精英文化的失落使中国文化艺术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漫长时期里走入低谷,丧失活力和创造力。对这个现实没有深刻的反省,将大大有碍于中国现代文化的建构。而当前最迫切的使命,是重建中国的精英艺术。

图为郎绍君。
概说与价值分析
精英艺术是文明社会和文化精英所创造、以文化精英为主要对象的艺术。一个时代和国家的精英艺术,以审美创造的方式表现着人类心灵和智慧所能达到的文明程度。
灿烂的文化离不开劳动者的创造,也离不开社会文化艺术精英的创造。如果没有文化精英群的出现,人类也许永远不能脱离蒙昧阶段。
文化精英不是天生的,也并非某些人自封或捧出来的。精英艺术品的生产不属于特权者的专利,其接受者也不是一个十分确定的已知数。精英艺术及其接受层是一个相对的范畴,它们具有稳定性,同时又流动着,追求着变异与升华,向未来敞开着大门。
譬如,王维为自己和士大夫文人而画,也为寺院或宫廷挥毫;陈老莲以画自娱自遣,也画通俗的酒牌和戏曲插图;吴道子曾浪迹寺庙,后来入了朝廷。但纵观一个艺术家的行迹与创作,总可以给他确定一个基本的归属。
精英艺术的独立性和价值是与社会文明的历史时序大体一致的,即在文明社会早期,精英艺术和宫廷艺术、世俗艺术、宗教艺术及民间艺术不大分得清,它们往往交织、重叠或混合着。在西方,自觉以文化精英为主要对象的艺术,是在文艺复兴以至启蒙运动后才鲜明呈现的。在中国,则是宋代以后才成为自觉,在上古、战国和两汉,分不清文人和艺匠,接受者也无所谓雅与俗。经过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的分化,艺术创作才逐渐拉开文人与宫廷的、民间的距离,但也仍然相互联系着或局部重叠着。
人类对精英艺术的认识,是随着精英艺术从一般艺术分离、独立并高度发展的历史而由不自觉到自觉的。但在某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业已自觉的精英艺术观念也可能中断或泯灭。
简而言之,精英艺术可大略用以下三条标准去衡量。
第一,它更深刻地体现着人类的精神性。它往往深刻地揭示出人的存在、意义和危机性。用雅斯贝尔斯的话说,就是有着“形而上的内容”,“其形象创作揭示出潜隐的实在的艺术”而不仅仅是追求快悦、不领受悲痛与历史重负的、装饰人生的艺术。
第二,它有明确的自律意识、创造意识,集中表现着人的灵性和驾驭语言符号以传达内在信息的能力。
第三,它最鲜明地体现着民族文化的过去与未来,揭示出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特色与变异,反映民族文明与外域文明的内在联系与差别。不复制古人,也不仿造外国人,但在它独特的艺术个性中,又总是融会着一切有价值和目的性的文化因素。
完全具备这三条的精英艺术是极个别的,只有那些杰出大师在他们旺盛创作年代才可能奉献出臻于完美的不朽之作。大多数精英艺术不会是完满的,但如果与上述三条不沾边,它就绝非精英艺术。在现代社会,经常会出现某种虚幻的假象,使精英艺术处在扑朔迷离中。社会地位、名声,以及拥有观众的多寡、时髦性、销售状况等,可以使冒牌货畅行无阻。
精英艺术应当拥有声望、观众与高售价,但事实往往并不如此。这正和文化精英人物的思想和行为往往不被时人理解相似——在许多情况下,可以用“曲高和寡”“不入时流”来概括。梵高、塞尚、龚贤生前都贫困潦倒或不被承认,认定他们的艺术价值的,是时间和历史。另外,在某个时期、某个地域,精英艺术并不平均分配在各种艺术样式中,古希腊是雕刻与悲剧,中世纪是哥特式建筑,文艺复兴是绘画与雕刻;唐代以诗为最,宋代是绘画和词,元代是绘画和戏曲……也许上天从不喜欢平均主义,在某个时空环境里,总是偏爱某一种或几种造物,致使偶然性大行其道。
崛起复又失落
清末民初,传统的精英艺术颇为衰竭。从五四运动到抗战初期,现代中国的精英艺术应运而生。它的特点是,以科学、人文理性为背景的新的个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尺度,以云集大都市(上海、北京、广州等)职业自由的知识层为主要作者来源和对象,用开放的心灵面对存在,把西方近代艺术作为主要参照系,并呈现出多元、探索、新旧杂陈、朦胧清新的资质。与它们相并存的,还有感应着时代变迁、对旧有艺术模式加以改革推进的传统精英艺术——如吴昌硕、陈师曾、齐白石、黄宾虹的中国画。
部分新的精英艺术家寻求摆脱对古代文化的传统态度,冲破宗法集体主义的罗网,寻求独立人格和创造的主体意识;他们从文化的高度观察具体的艺术现象,以高屋建瓴的姿态择取中西传统,既不亦步亦趋地模仿,也不在小情趣中陶醉自足。因此,他们既超越了自生自灭的民间艺术家,也超越了封闭在固有模式里的文人士大夫艺术家。
从新美术的倡导者蔡元培、康有为、鲁迅、陈独秀、吕澂,到一批开风气之先的艺术家如高剑父、刘海粟、徐悲鸿、林风眠、颜文梁、丰子恺、庞薰琹等,莫不如此。刘海粟为了艺术的信念起而与军阀孙传芳抗争;徐悲鸿在出国留学前就抱定了兼取中西以改造中国美术的宏愿;林风眠在法国组织“霍普斯会”,要“以我入地狱”的精神沟通中西艺术,“为中国艺术界打开一条血路”。尽管他们在当时不过是20余岁的青年,却能够雄视千年,以普罗米修斯的胆略和牺牲精神,担负起创造新文化的历史使命。他们雄姿英发,东渡日本,西赴欧美,开学校,创学派,立画会,筹美展,办刊物,发表宣言,著书立说……其心灵的开放、人格的独立、精神的坚韧、创造的气魄集中体现着觉醒了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性,体现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他们追逐广博的学养,兼习东西两大艺术传统,努力把自己塑造成艺术文化人。
举例说:李叔同兼画家、书法家、音乐家、戏剧家与佛学大师于一身。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除兼善中西绘画外,还都治史论,又是社会文化活动家、教育家。丰子恺兼通美、音、文字与翻译,闻一多是画家、诗人、学者,李金发是雕刻家、又成为中国象征派诗歌的鼻祖,傅雷是艺术评论家、翻译家,倪贻德亦兼小说家、画家和理论家。像这种通才式的杰出人物还可以数出许多,如陈之佛、傅抱石、宗白华、吕澂等。不妨说,艺术文化人集群的出现,正是精英艺术、精英文化的重要标志。
不错,他们在某一门类艺术的形式语言修炼上大都不太精粹,甚至幼稚粗糙,但这是社会文化转型期的精英艺术不可避免的。不成熟的一代新风开拓者的历史地位绝不亚于只在既定模式中精益求精的艺术家,因为正是他们给20世纪的中国艺术注入了新的文化意识——这是比形式的成熟性远为重要的东西。
林风眠早期作品的人道主义和后期作品中的诗意孤独,徐悲鸿作品对侠义精神、悲悯情怀和家国命运的深切关注,丰子恺的佛心与父爱,“决澜社”浪子们“狂飙一般的激情”,都折射着五四的启蒙精神。而蔡元培的“美育说”、鲁迅的“为人生而艺术”、宗白华的“境界说”,以及滕固、邓以蜇、郑午昌、倪贻德、傅抱石、陈抱一的美术研究和评论,更以理性的成果表现着精英艺术在思想、情感方面的独立性和青春活力。
抗日战争爆发后就不同了。精神形而上的思索和个性情感的悲欢体验渐渐让位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和“走出象牙之塔”的呼声。投笔从戎,宣传鼓动,文化下乡,中断画室书斋的创造,一切都服从于救亡之需。那么,五四精神还坚持不坚持呢?由是便引发了“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一种意见认为,民族形式应成为文艺形式的正宗,而民间形式则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并由此而推定“民间文艺为中国文学的正宗”。
另一种意见认为,救亡宣传不能丢掉反封建的启蒙任务,救亡文艺也应具有民主性的时代特征,因此,过分抬高民族形式和民间文艺、贬低甚至否定借鉴外来文化的观点就背离了五四精神。在文艺与大众的关系上,前者强调“大众化”,后者强调“化大众”:即一个要求以大众普及艺术改造或取代精英艺术,另一个要求以精英艺术引导大众普及艺术。
再生与困惑
与改革开放同时出现的,还有个性意识的觉醒、人的价值的寻找、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批判。思想与创造的自由、多元趋势,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确认。这一切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何其相似!星星美展、朦胧诗、伤痕文学、探索影片、新潮美术和各类被称为“实验”“前卫”的艺术,各种探索与尝试,一浪逐着一浪,使人们应接不暇、错愕相顾。中年一代在徘徊中自省、蜕变,青年一代呼啸着弄潮击浪,重新观看与思考周围的一切。怀疑、批判、挑战,背起历史的重负,体验生命的悲剧情境,凝聚成新的精英力量。精英艺术的复苏与重建,势在必行。
精英艺术的重建不免艰难曲折。幼稚、粗糙、模仿性、双重性格、伤痕、病态、牺牲,都会重叠在它的起步甚至升华过程中。它的周围,也难免不绝于耳的呵斥、诅咒和嘲笑,至于孤独和苦闷,大约会永远与它相伴。
但是,它从一开始便与既往的通俗大众艺术有深刻区别——第一,是对艺术精神性的追求;第二,是对革新语言符号的创造性探索;第三,是艺术自律性(不单指形式)与独立性意识。这三个方面赋予它们以闪光的生命力:在历经蜕变、自我反省和种种磨难之后,就会走向成熟。相应地,将会有一批杰出的艺术家、理论家和伟大作品出现,风格流派在纷争中各自独立发展,精英艺术在整个艺术格局中的领导地位将被确认。也许这还要有一段十分艰难的历程,但它终归是要出现的,因为这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化的可能,也是迫切需要。
除了自身的粗糙和脆弱性之外,当代精英艺术面临的最大困惑是一种新的通俗大众艺术的挑战。自从商品经济再次繁荣以来,艺术生产与消费就急切地向商品和金钱求爱。销售、出版、展览、演出甚至艺术家本人的身价,都不能不接受营利的无情检验。
对购求者的适应乃至迎合旋即成为生存发展的需要。主要消费对象是城市中等文化群众及被商品大潮卷入城镇、逐渐市民化的农民,还有海外的旅游者和画商(多非收藏家)。他们的鉴赏需求主要是以欢悦、刺激原则制造的艺术品,或者可作为中国“土特产”“观光纪念品”的行货。因此,与牛仔裤、迪斯科一起流行的,是流行歌曲、美人挂历、月份牌年画、娱乐片、言情小说、暴力文艺、甜俗的油画、复制性的中国画、种种小工艺品等,金钱的魅力使通俗文艺大行其道。
为了迎合顾主,大批艺术家降低标准求售,放弃艺术与精神性的探索,营利、畅销也成为一些出版、展览机构的方针,大量艺术品转换为复制品,纯粹的创造更加孤立。可以说,这种俗化艺术虽然给作者与消费者带来舒适快乐,但其本性却是和艺术的精英性相背离甚至敌对的。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这种通俗艺术也泛滥成灾,但它们有补偏的办法,那就是把精英艺术和通俗的行货区分开,把以获利和单纯娱悦为对象的展销和艺术收藏分开,把咖啡厅艺术和音乐厅、博物馆艺术分开。中国尚无成熟的以文化中产阶层为主顾的艺术消费对象,又没有建立起销售艺术品的管理体制与规范渠道,精英艺术只好和通俗行货一同涌入市场。
艺术家面对着两难的选择和人格的分裂。中国知识分子的劳动报酬如此之菲薄,今天借通俗艺术挣些钱,让生活好些,难道还有可指责的吗?而且,没有经济的自立就无法维持再生产,难以支撑人格思想的自立。
可是,降格、阉割自己的才能与创造性,使精英性沦丧,不是更悲哀的事吗?一面是通俗艺术作者的红火富有,一面是精英探索者的贫穷孤寂;一个吮吸着欢乐,一个品味着痛苦。如何克服这种两难和分裂的境遇呢?
我想至少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做起:一是纯化与强化精英艺术。这需要艺术家自己与文化精英层两方的努力,包括国家文化艺术部门的支持。要自重、自爱,保持精英艺术的严肃性,克服嬉皮士、雅皮士式的“玩艺术”行径,坚持不懈地探索、追求下去,这是精英艺术家走向成熟的基本条件。二是提高通俗艺术的水准。要建设高层次的精神文明,就不能满足于大众化,还必须“化大众”,用高尚、纯净的精神产品提高大众的素质。在现代中国,完全用商品规律支配文化艺术的生产与消费是危险的。三是艺术家在目前时期可以过“两栖生活”,兼通俗艺术与精英艺术创作于一身,把挣钱与艺术追求尽可能区别开来。精英艺术与通俗艺术并无绝对的界限,精英艺术家创作通俗艺术作品,有益于通俗艺术的提高,问题在于精英艺术家不能一味地降格迎合。四是提倡精英艺术与通俗艺术的结合,即把探索性与适应性、精神性追求与娱乐性满足融为一体,创造出一种兼具两种品质的作品。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美术评论家,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近现代美术研究室主任;本文为新时代美术高峰课题组、中国画“两创”课题组专稿)
《人民周刊》2024年第15期
(责编:汪翠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