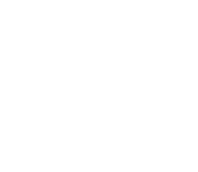世人对“笔墨当随时代”多有误读
多年来,我一直提倡“笔墨当随古代”。因为清初石涛提出“笔墨当随时代”。如果说,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笔墨,这是对的。但这个“随”字,有可能被人理解为跟随、追随,甚至理解为要学当时人的笔墨,那问题就严重了。因为当时的笔墨五花八门,有的故作新异,有的以丑怪为新,等等。这些内容没有经过历史的考验和筛选,有可能就是糟粕。古代留下的传统,都是经过历代文人画家的筛选,经评定为优秀的内容。陈独秀撰写《孔子与中国》时,引用尼采的话“经评定有价值始有价值,不评定价值,则此生存之有壳果,将空无所有”。古代的传统是经评定有价值者,当时的东西还必须接受评定。或曰:笔墨如果一直都随古代,岂不陈陈相因,一成不变,千载一法,艺术不就真的终结、死亡了吗?所以,还必须知道笔墨表现什么。知道了笔墨表现什么,笔墨就不可能一直一样。这正如写律诗,出句和对句的平仄要相对,即平平对仄仄,这是一个原则。但总是相对,第三句就和第一句相同了,这就要有粘,再加上韵脚的不同,所以,每一句的平仄就不可能完全相同。
知道了笔墨要表现什么,更如知道律诗的格律是一定的,只要是律诗都必须遵守,不能出一格。但诗的内容不同,千诗万诗都不会相同。唐诗、宋诗、元诗又都不相同,诗还是在发展。
传统笔墨须表现新的时代精神才能出佳作
传统的笔墨必须表现新的精神、新的时代精神,才能产生好的作品。历代优秀的作品皆如此。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北宋、南宋、元、明清,都是延续传统的,但历代绘画皆不同。据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及《法书要录》所记,中国的绘画与书法,都是代代相传的。如书法,蔡邕“传之崔瑗及女文姬,文姬传之钟繇,钟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王羲之传之王献之,王献之传之外甥羊欣,羊欣传之王僧虔,王僧虔传之萧子云,萧子云传之僧智永,智永传之虞世南,世南传之欧阳询,询传之陆柬之,柬之传之侄彦远,彦远传之张旭,旭传之李阳冰,阳冰传徐浩、颜真卿、鄔彤、韦玩、崔邈……”(《法书要录》卷一《传授笔法人名》)。但历代的书法并不相同,相反,不在这个传授之列的书家,鲜有成为大家的。《历代名画记》卷二《叙师资传授南北时代》中记载,从曹不兴、卫贤到顾恺之,张墨到曹霸、韩幹、陈闳等,也都是历代相师,但画风并不相同,而且代代都在发展。
历史上艺术取得巨大成就者多倡导“复古”
还有更严重的问题,历史上凡是提出“复古”口号并付诸实践的,在艺术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都产生了不朽的杰作。我曾在《复古也是一条路》一文中谈到这个问题,无论诗文抑或书画,凡是高举“复古”大旗的,成就皆十分突出。唐朝韩愈和柳宗元是倡导古文运动的两大领袖。韩愈说:“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他还说:“愈之志在古者,不惟其辞好,好其道焉尔。”柳宗元也如此。宋朝欧阳修也是力倡古文运动的,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宋朝的文学也是从欧阳修的古文运动开始有了相当大的起色,唐宋八大家都是古文运动产生出来的。
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也是“复古”运动,他们打出的旗号就是“回到希腊去”,要“复兴”古典文化。“文艺复兴”是后人无法超越的。可见,“复古”是有何等的效力。
中国美术史上,宋元绘画为两大高峰,我在《中国山水画史》一书中说宋朝的绘画史“从保守到复古”。元朝初,赵孟頫就力排“近世”,而极力倡导“复古”,他把“古意”列为绘画审美的第一标准。从此,以“古”为“高”,称为“高古”;以“古”为“雅”,称为“古雅”。
思想界重要人物孔子、老子、庄子,也都是提倡“古”的。孔子自云“信而好古”“好古敏以求之”,其言必称西周,“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孔子是当时提倡“复古”的代表。老子言必称“小国寡民”,“使人复结绳而用之”,“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考古学谓“结绳而用”当在夏之前,则老子主张复古复到尧舜时期。而庄子之徒力主“巢居”“与麋鹿共处”,甚至“民知其母,不知其父……此至德之隆也”。庄子主张复古要复到原始时代。
“复古”是学古人精神而非重复古人形式
历史上的“复古”大多是学习古人的精神,以去除当时的浮华风气,创造出更优秀更实在的时代或艺术,而不是重复古人的形式。韩愈还提出“陈言之务去”,他是以“复古”为武器,扫除六朝的浮艳之风。北宋复古的青绿山水也远比以前的青绿山水要充实丰富得多。元人复古学五代的董、巨,显然又不同于董、巨,而创造出元人的特点,元人的绘画也正是继五代之后的另一高峰。
“笔墨当随古代”,其实是当随传统,这是古代的传统,而不是现在的新传统。因为石涛说“笔墨当随时代”,所以,我提出“笔墨当随古代”以对之、以强调之。
石涛说的“笔墨当随时代”,似乎也是质疑的提法。石涛的笔墨就没有随“时代”,清初的时代笔墨是“四王”一系,他就没有随之,相反对“四王”一系笔墨不敢越“南宗”一系雷池而大加嘲讽。他说:“画有南北宗,书有二王法……今问南北宗,我宗耶,宗我耶。”“万点恶墨,恼杀米颠,几丝柔痕,笑倒北苑……”这都是针对“当代”的流行笔墨而言的。
清朝画道衰落,“四王”一系并没有创造出宋元那样的高峰,可能和他们笔墨未随古代有关。“四王”口中说的是学古代,画论中也提古代,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学古代。王时敏学的是和他同时代的董其昌,后“三王”学的是王时敏和董其昌。他们所谓学古代其实都是学董。从明末的董其昌到王时敏,再到王鉴、王石谷、王原祁,再到“小四王”“后四王”,都是“笔墨随时代”的,不是逆向学古代,而是顺向学时代(当代)。当然,“随时代”“学董”也未尝不可,这和他们不善学也有关(此当另论)。
书法更是如此,如果立志成为一个书法家,必须学“二王”、学“颜柳”、学周秦、学两汉、学帖、学碑,总之必须学古代。如果一直学当代的流行书风,甚至学那些用鬃刷笔刷出的工艺字,再加上一些红绿点子,那么前途只是死路一条,终其一生,连书法家的尘迹也看不到。
先入古再出古是书画大家自我成就之路
为什么笔墨不能随当代(时代),而非要随古代呢?其一,当代的笔墨良莠不分,未经过历史的筛选;其二,即使学的是优秀的笔墨,而当代的笔墨为当代人所常见,就容易千篇一律、千画一面;其三,当代人笔墨又分两种,一是传承古代的,二是创新的。学当代人传承古人的,不如直接学古人的。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故为其下。学创新的,当然学得好也未必不可。齐白石成功了。很多人学齐,形成齐派,但超过齐白石的就十分少,甚至不可能。还有些所谓创新的笔墨,未经时代的检验和过滤,未必是优秀的笔墨。古代留传下来的优秀作品都是历经筛选,以及历代专家公认的。所以,一般不会学坏。学得正确,绝对不会坏。
西方画要技术,中国画要功力,功力是技术的升华。与中国武术一样,要想有功力,就必须按传统的方法去练,否则永远不会有功力。
进入传统,出不来怎么办?这是不可能的。董其昌说:“未有学古而不变者也。”历史上八大山人的画,笔墨功力最深厚,个人风格也最强烈。八大山人进入传统最深,他笔笔入古人、笔笔出古人。黄宾虹笔笔来自传统,但笔笔有新意。历史上还没有一个书画家深入传统而跳不出来的。若能进入房间,必能出来,就怕进不去。所谓“进去”,就是把传统学到手,只要有思想,只要生活在新时代,用传统的手法表现新的时代精神,必能创作出新的精神。
倡“笔墨当随古代”以匡时弊
经常看到一副对联:“立志不随流俗转,留心学到古人难。”“不随流俗转”,就是不同于流行风气,这流行风气都是当代的。“学到古人难”,即学到真正的传统难。由此可见,唯难而能之方可贵。
优秀的书画家必须先学到古人的笔墨传统,这是功力的根本,再来表现新的时代精神。因为要表现新的时代精神,古人的笔墨又不够,这就必须充实加强古人的传统笔墨,然后又成为新的传统。传统也在流变,犹如长江浩荡,每一处水质、水波、深浅、宽窄、缓急,都有区别,但源头是不变的。源头的水来自雪山,雪山也是大自然的积化。但没有这个源头,就没有浩浩荡荡、一泻千里的长江。
源头一断,主流就干了,而支流的水有限,不但无助于主流,而且不久也会干枯。若不要长江,重新挖一条新流,能和长江比吗?
早在南北朝时,姚最就提出“质沿古意,文变今情”。元朝的赵孟頫在《兰亭十三跋》中说:“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接着又说:“右军字势,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然古法终不可失也。”字体可变,但用笔(即笔墨传统)千古不变。“古法一变”,是指字势变了;“古法终不可失也”,即笔墨当学古代也。赵孟頫又说:“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也就是“笔墨当随古代”,或者说“笔墨当随传统”。
时至今日,没有传统的文化,都是浅薄的文化。
朱子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传统也要在新时代“加邃密”,新知中必涵养旧的传统,才能深沉。善学者能于旧学中知新知,于新知中见旧学,则旧学亦新知,新知亦旧学也。
编辑见余,即索文于余。余正养病金陵,乃强书数语,唯倡“笔墨当随古代”,以匡时弊耳。
(本文为新时代美术高峰课题组、中国画“两创”课题组专稿)
(《人民周刊》2024年第12期)
(责编:汪翠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