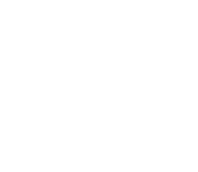西方艺术让我回归中国水墨意象
书法是意象,无“表意”无书法
当下,一谈到中国书法、中国画的创新,不少人考虑的是艺术形式的创新。从目前来看,借鉴和模仿西方艺术,尤其是从观念到形式模仿西方抽象艺术成为一部分人的选项。
曾有中国美术理论家将人类绘画艺术的发展路径总结为:由具象到意象,由意象到抽象。其实,抽象绘画只是西方艺术发展中的一个阶段,而绝非人类艺术的必然路径选择。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借鉴西方艺术的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等现代抽象技法结合于中国画的格调与气韵,创作了一批新作。这些作品在香港的一家艺术杂志上发表后,受到西方艺术机构的关注,由此我受邀在日本、英国、美国举办画展。
出国举办画展,进行文化交流,开阔了我的文化视野。其间,参观了很多国家的艺术,对西方从古典到现当代艺术有了全方位直观了解与感受。特别是在英国伦敦的泰特美术馆参观了西方印象派、表现主义、抽象画派最具代表性的大师的原作,对我触动极大。这些代表了西方艺术高峰的大师的作品主要是半抽象,以神为主,有激情,有笔触感,这些特征类似中国写意画,异曲同工,应同属于意象绘画。
相比较,西方意象重色彩,有张力,画面满实,讲究动态美;东方意象则是受玄学与佛学影响,重内在精神,主静,空灵,墨分五色。
从西方办展回国后我选择了回归,回归东方水墨意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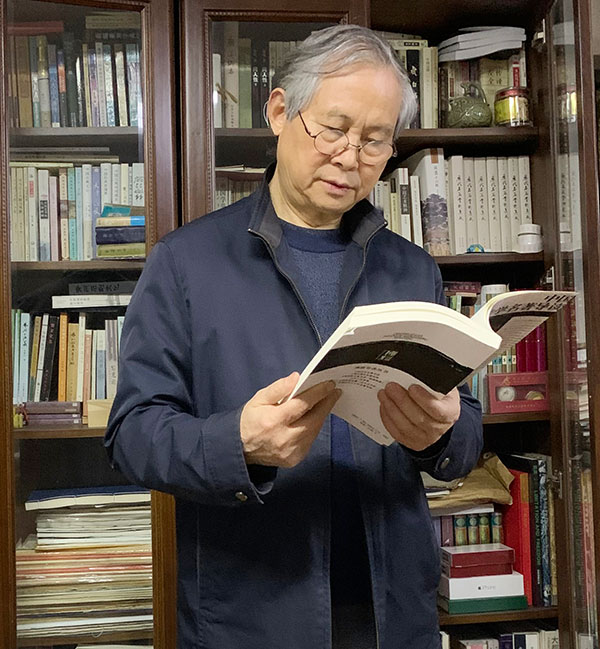
中国艺术的核心是意象,意象即写意。写意是半抽象,其抽象的形式语言探索是必然,但抽象的形式语言并不等于纯粹的抽象绘画。
实际上,中国人对抽象形式精神认识与表现的强度绝不亚于西方抽象艺术,而且历史更悠久。
中国古典哲学孕育了中国的文化艺术,中国书法与中国哲学同源同根,中国哲学与中国书法的抽象思维始终伴随着中国艺术。
当中国古代文字在超脱于象形阶段之后,就发展成为一门具有抽象形式与意味的书法艺术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字均不被称为艺术,唯独中国书法是一门从理论到实践、从艺术程式到品评标准,具有一套完备学术体系的艺术。
中国书论中对于抽象艺术形式体验的描述在书法史中俯拾皆是。
东晋女书法家卫铄曰:“‘横’如千里之阵云,隐隐然其实有形。‘点’似高山之墬石,磕磕然实如崩也。‘撇’如陆断犀象之角。‘竖’如万岁枯藤。‘捺’如崩浪奔雷。‘努’如百钧弩发,‘钩’如劲弩筋节。”
西晋书法家索靖在《草书势》中说:“盖草书之为状也,婉若银钩,漂若惊鸾,舒翼未发,若举复安。虫蛇虯蟉,或往或还,类婀娜以羸羸,歘奋亹而桓桓。及其逸游盼向,乍正乍邪,骐骥暴怒逼其辔,海水窊隆扬其波。芝草蒲萄还相继,棠棣融融载其华。玄熊对踞于山岳,飞燕相追而差池。”
孙过庭《书谱》有言:“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资,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信可谓智巧兼优,心手双畅,翰不虚动,下必有由。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芒。”
由此可见,中国书法中的抽象思维与抽象形式语言是何等丰富鲜活!何等仪态万方!何等玄奇夭娇!
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原则认为,宇宙规律为阴阳之道,一阴一阳谓之道。中国书法无论是意与象,形质与神采,以及书写过程中极为丰赡的笔势运动的转换与呈现,无不是阴阳互动与矛盾的对立统一。
书法是中国艺术中的艺术,其抽象的形式思维影响到中国艺术,包括中国的绘画、戏曲、音乐、舞蹈、园林建筑等。中国画写意之“写”,书法也。借书法笔墨来表现绘画作品中的诗意与抒发作者情感。
中国书法具有抽象艺术的形式与意味,但它始终与文字的“表意”相结合。因此,中国书法是意象,而绝非类似西方艺术的纯抽象。书法一旦脱离了书写中文字的表意,而成为纯抽象的墨线、墨块、墨团,那就不是书法。“表意”是分水岭,无“表意”无书法,这点上不能含糊。
意象指向精神,常表达哲思
抽象指向形式,常不知所云
2000多年前,欧洲美学思想的重要奠基人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中提出:一切艺术产生于模仿。模仿就是写实,就是具象。模仿以物为主,心必须服从于物,重在模仿自然,于是后来西方绘画便产生了以科学的解剖学、透视学为依据的素描。19世纪60年代西方艺术出现了印象派,七八十年代达到了鼎盛时期,印象派画家对科学的光与影是那样的着迷,印象派和表现主义绘画是半抽象。20世纪中期,西方艺术出现了以波洛克为代表的抽象绘画。
当西方杜尚的《泉》(小便池)出现,便彻底颠覆了西方之前的绘画艺术,当然也颠覆了抽象艺术。西方艺术又相继出现了观念艺术、现成品、装置艺术、行为艺术、大地艺术、光效应艺术、波普艺术、人工智能艺术等。
西方艺术倾向科学。
否定过往传统,打破现存艺术是西方“否定之否定”的哲学观,并由此而派生出了颠覆式的创新。不少人将追求创新的绝对性视为西方当代哲学的基本精神。
中国艺术倾向文化。
中国艺术重比兴,传统说法中比、兴的核心是托物言志。不直言其志而以物喻之,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比兴说的理论最早见于两千多年前汉代的《诗·大序》:“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南朝刘勰《文心雕龙·比兴》亦云:“比显而兴隐哉!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唐代僧人、诗人皎然《诗式》则言:“取象曰比,取义曰兴。”宋代朱熹亦有所论:“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比兴说重在想象,不拘泥于自然的写实,而重传神,是以“寄情于景”“托物言志”为表现手法,在表现自然时可以联想、移情、省略、夸张,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意到笔不到,给观者留下想象空间,这就是中国画的写意,也即意象。
中国古典文论中就有“大象”“立象以尽意”之表述。《周易·系辞上》曰:“圣人立象以尽意”,立象以尽意是《易传》的重要哲学、美学观点。南朝刘勰《文心雕龙》曰:“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可见中国艺术很早就已将主客观相融合的“意象”作为艺术的创造法则与精神追求。中国书法、中国画、中国戏曲、中国音乐、中国舞蹈,包括唐诗宋词等,均是表现主客观相交织的“意象”,将自我之情性、学养于自然物象的表现之中,流露出物我交融、天人合一的人文关怀。
抽象指向形式。西方艺术更强调形式美,总是在形式上不断地转变与翻新。
意向指向精神。中国艺术也强调形式美,但同时更看重其内在精神价值,通过其艺术呈现出一种哲理,以及自我的心灵表达。
具象与抽象可视为艺术形式的两端。具象是写自然物象之真实,抽象是脱离了自然物象的纯粹形式符号。具象容易使人司空见惯,可熟视无睹。抽象往往让人不知所云,只能靠作者自说自话来自圆其说,自圆其说“讲故事”是西方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
颠覆式发展导致西方艺术时有中断
“中和”使中国艺术发展传承有序
中国文化精神的高深妙谛是参透大化生机的无为而为,以及由此而派生出的“中和”之理,“中和”是中国文化的最重要标准之一,中国艺术体现“中和”精神的正是意象。
意象是在具象与抽象之间,中庸方显其大,具象与抽象两极之间有巨大开阔地带,留下的是画家的想象空间、情思散发的空间、艺术形式的表现空间、艺术观念上的回旋空间,以及大众能在精神上自主参入其中的审美空间。
两千多年来,中国哲学的“意象”理念早已成为中国文化血脉不断,以及中国艺术蓬勃成长的不竭的艺术创作源泉和精神源泉。
西方艺术发展是颠覆式的发展,容易走向极端,纯抽象是极端,极端就没有余地了,所以西方艺术所表现出的碎片化、不断翻新,也因此时有中断。
中国文化的“中和”精神决定了中国艺术的发展是继承式发展,它每前进一步都是需要向后一次的循环往复,如此生生不息。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文化复兴都是返回经典,返璞归真,从经典再出发。因此,中国艺术传承有序,发展创新,始终保持了其完整且鲜活的文化形态。
“流美者,人也。”(三国·钟繇《笔法》)一画之迹呈现宇宙万象来表现人性的真善之美,呈现人性、人格之光辉。艺术家徜徉于自然之间,参悟自然、钩深致远,直透内在生命精神,呈现生命气象,激发余蕴无穷之神思,点化万物,激励人心。艺术作品的背影折射的是艺术家自身的人,书如其人,画如其人,在这一点上,唯东方意象艺术表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艺术以境界为上。何谓“境界”?我理解境界即诗,主客观融为一体,优游涵咏,“达其情性,行其哀乐”,“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孙过庭《书谱》)何谓“风骚”?周风楚辞中伟大的大写意与抒情传统是也!
总体而言,中国文化显得更加深厚,而不那么简单,不那么直白,而更显曲折、委婉,更加多情,更加耐人寻味,也更加智慧。
西方抽象艺术生发于西方的文化土壤与哲学思维,而东方艺术中的抽象表现存在于东方意象的哲学观念之中,它根植于中国的文化土壤。
中西方艺术表现的某些趋同性是基于人类对真善美的普遍认识,而表现出的不同则体现了各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基因的根性差异。这也正是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与人类文明的丰富性之所在。所以,在中国艺术的发展与创新中,包括学习与借鉴西方艺术,应以我为主,适当吸收,不伤国体,遵从民族艺术的发展脉络与规律,在继承中创新。
各民族历史不同,文化观念不同,气质趣味不同,艺术风格也会不同。同此理,时代不同,每个人的气质趣味不同,文化需求与观念不同,艺术风格也会不同。
东方意象绘画以其强烈的主体意识和奔纵潇洒的笔墨特色,风标别具,数千年延绵不断,是世界文化中最值得探究的奇观。中华意象艺术何其美哉!何其妙哉!何其大哉!
(作者为中国国家画院、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艺术院特聘研究员,国家一级美术师;本文为新时代美术高峰课题组、中国画“两创”课题组、中国书法“两创”课题组专稿)
(《人民周刊》2024年第4期)
(责编:汪翠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