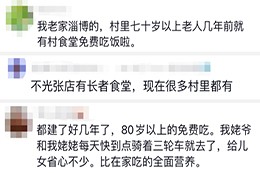费正清,20世纪最负盛名的海外汉学家和中国问题观察家之一。他曾以不同身份5次来华,亲历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历史,开创“哈佛学派”引领国际汉学研究,参与中美交往诸多事件。有学者评价费正清:“在重建美国和中国的学术交流中处于圣贤和使者双重角色的地位”,美国现代中国学奠基人和中美关系学界“头号中国通”,在西方史学界和外交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感恩“老师蒋廷黻的帮助”
费正清学术生命的开端,与早年在北平的4年经历紧密相关。1931年,正在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费正清,开始关注现代中国问题。为了完成博士论文,他申请英国大学声誉最高的罗德奖学金,成为该奖学金第一位到远东地区做实地研究的学者。
1932年初,25岁的费正清启程来到北平,和夫人威尔玛住进了西总布胡同的四合院,邻居便是留美归来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他们志趣相投,“互相为对方打开眼界”,将对方视为“最亲密的朋友”。梁思成给他取了中文名字“费正清”,意为“正直清白”,与本名John King Fairbank音义同具;梁林夫妇还为威尔玛取名为费慰梅,同样含义隽永,使费正清夫妇充分感受到中国文字的魅力。费正清夫妇还和梁林二人到山西考察中国古代建筑,酷爱艺术的费慰梅后来成为中国营造学社的外籍名誉会员,这些经历无形中启发了费正清研究现代中国学的思路。
到北平不久,费正清结识了许多留学英美的文化名流。1932年5月的一天,费正清应邀到“北平八大楼”之一的东兴楼饭庄会见胡适、丁文江、陶孟和等人。与他们的交往,费正清对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界有了初步认识。他还结识了宋庆龄、蔡元培等著名人物,加深了对中国社会的了解。而带他步入现代中国学术研究殿堂的,则是历史学家蒋廷黻。蒋廷黻的治学培养方式,以及后来为抗战救国而弃学从政的经历,也在一定程度影响了费正清。
蒋廷黻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注意收集新材料,推动影印出版晚清档案,为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开辟了一条新路。在蒋廷黻指引下,费正清开始接触中国近代史档案,为他以后搜集和运用中国史料打下坚实基础。1933年,费正清因奖学金到期,积蓄即将用光,蒋廷黻又引荐他到清华大学任教,费正清得以“第一次走上讲坛”。他讲课节奏很慢,发音清楚,强调重点,每句话重复两遍,“我的许多学生认为上我的课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英语口语的机会。这时我正在学习历史,所以我们双方都很满意”。
费正清的首次中国之行,足迹遍及华北、华东和东南沿海一带,广泛接触中国现实社会,完成博士论文《中国海关的起源》的写作,确立了自己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学术方向。30多年后,他在北京饭店动情回忆:“在我是一名学生的时候,曾受到老师蒋廷黻的帮助。”他感念这份“恩德”。
两返中国
1936年初,费正清回到美国任教哈佛大学。1941年8月,费正清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被征召到华盛顿情报协调局(美国中央情报局前身)。1942年9月至1943年12月,他以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的身份被派到中国;1945年10月至1946年7月,他担任美国驻华新闻处处长,开始了他学人从政并成为“头号中国通”的政治实践。
第二次来华正值抗战后期,费正清见证了内忧外患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屈坚守。当他与昔日清华故友在西南联大重逢,教授们仅能糊口的贫困状况让他极为震惊。他来到金岳霖、陈岱孙的住处——美国领事馆隔壁的旧剧院露台,“在我们坐着谈话时,一只硕大的老鼠穿过纸糊的天花板,差点掉下来”。他拜访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看到梁林夫妇生活艰难,人也非常瘦弱。费正清夫妇通过各种渠道,从美国把药品和其他贵重物品(派克钢笔、手表),“以工资补贴的方式”分发给中国学者们。当时梅贻琦校长的工资每月不到600元,而一支派克钢笔的价格高达6000元。
1943年6月,费正清结识了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的新闻发言人龚澎,随后结识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11月8日,费正清与周恩来初次见面,很快被周恩来的非凡魅力和卓越能力所折服,“他英俊帅气,眉毛浓密,智力超群,直觉敏锐。在我们用汉语谈话时,时不时也说一些英语”。
费正清第三次来华时,目睹了抗战刚结束时国民党当局的贪腐。他往返在中国各大城市,加深了对中国混乱局势的认识。为此,他提醒美国政府,不能简单地将国民党政府视为盟友,主张与中国共产党尽快建立关系。
为了答谢以费正清为首的美国新闻处,重庆中共代表团在重庆胜利酒店举办了盛大的鸡尾酒会。费正清后来回忆:“周恩来唱起了歌,我们也跟着哼唱起来……他们唱起了延安歌谣,互相敬了几次酒后,我们也唱起了美国内战时期的歌曲。”
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
1946年7月,费正清返回美国重拾教学科研工作。9月,他发表反思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文章《我们在中国的机遇》,力图纠正美国对华政策。他将两次到中国任职的经历梳理成书,于1948年7月出版他的成名之作《美国与中国》,得到普遍赞誉。1955年,费正清创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研究以中国为核心兼涉中华文化辐射的东亚地区,开创“哈佛学派”,培养了1000多名研究者。
中苏关系破裂后,费正清不断呼吁全面研究整个东亚地区,加速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从越南撤军。基辛格曾与他就如何恢复中美邦交进行讨论。费正清从中国历史上的朝贡体制谈起,绕着弯儿说,毛泽东将会见任何登门拜访的国家元首,而美国总统出访则没有历史和现实政治上的负担,还送给基辛格相关文章和论文集参考。基辛格后来表示,“那次谈话改变了历史”。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打破了中美两国的对立局面。5月,应周恩来邀请,费正清夫妇一行6人,作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第一批美国文化人士访问中国。6月16日,他们在人民大会堂“迎客松”画前合影,周恩来回忆29年前他们在重庆初次见面的情景。费正清说起周恩来兴致勃勃演唱延安歌谣的情景,发现周恩来喜悦面孔下透出“久经磨炼的犹如钢铁一般的意志”。宴会持续4个小时,临别之际,周恩来用英语对费正清说:“明年或晚些时间再见。”可惜的是,周恩来当时已患膀胱癌,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对费正清来说,这次重返北京,“如同毕业40年的同窗聚会”。他与多年好友金岳霖、钱端升会面吃饭,见到了周培源、张奚若、陈岱孙、费孝通、邵循正等老友,但“最亲密的朋友”梁思成已在他们来华前4个月与世长辞,林徽因则早在1955年就因病逝世。龚澎也于1970年病逝。这次为期6周的访问,费正清走访了中国很多地方,感受到这片土地的今昔变化。
历史推进到1979年1月29日,中美正式建交后不久,邓小平到美国白宫访问。费正清作为30年来积极倡导中美关系正常化一派的代表,亲历了这一历史盛会。他被安排在宴会贵宾桌首桌,与邓小平有了一次简短对话。邓小平问他:“您贵庚?”费正清答:“72岁。”邓小平说:“我74岁。”费正清道:“但您还有头发,我却没有了。”邓小平幽默地说:“显然您用脑过度了。”费正清本想与邓小平一同追忆周恩来,但他这次错过了机会。
遗憾在半年后得到了补偿。8月,费正清应邀陪同美国副总统蒙代尔访问中国,这是他第五次中国之行。人民大会堂热烈的晚宴上,邓小平和蒙代尔走到费正清身边,高度评价他为恢复中美关系所作的贡献。费正清抓住机会,提议为纪念周恩来干杯,“我们碰了杯”,表达了对周恩来的怀念之情。
转变中国史观
费正清的学术观点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美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世界格局的调整,他的中国史观经历了“西方中心论”向“中国中心论”转变的过程。
20世纪上半叶,“西方中心论”在西方学术界广泛传播,费正清也深受影响。4年的中国求学经历,对中国历史典籍的刻苦钻研,他深刻认识到中西方文化之间本质上的差异,认为晚清中国正是因为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冲击,才逐渐由传统封建社会步入资本主义发展轨道。这种以西方冲击为动力开启中国近代化的“西方冲击—中国反应”模式,成为二战后解释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模式,推动美国“汉学研究”转变为“中国研究”,费正清也由此成为“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创建之父”。
在费正清看来,“用孔夫子的话来解释毛泽东显然是不够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他为核心的“哈佛学派”把中国研究引入美国各地大学课堂,他们关注风起云涌的亚洲革命,推行“官方史学”,并把“冲击—回应”模式作为主要分析框架,成为美国学术界中的一枝独秀,代表了美国的东亚研究和中国研究的最高水平,费正清也因此成为享誉中美关系学界的“头号中国通”。
费正清对中国史观进行反思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美国相继爆发反种族歧视、女权运动和国内反战运动,尤其是越南战争的失败导致美国对华遏制政策破产,这一系列问题暴露出美国的很多漏洞,他开始怀疑美国与西方文明的价值模式。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缓和,有利于他进一步摆脱冷战思维的束缚,更加全面客观地看待中国问题,从而更多关注到中国历史自身的发展动力。
标志着他思想转变的著作是《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他在书中写道:“中国的重心在内部,在中国人民中间,中国革命的构成因素也是在那里积累起来的。”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中国新史》,进一步强调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是由中国自身内因驱动,“如果我们要理解中国,第一件必须做的事是,避免用欧洲的尺度来判断”。这些新观点,修正了“冲击—回应”模式,表明了费正清中国史观的变化。
费正清的中国史观从突出西方文明作用的“文明冲突论”和“冲击—回应”模式,逐渐向突出中国发展内部动因的“中国中心论”发生转变,从一个侧面折射出20世纪中国革命的变化与崛起。尽管费正清总体上对中美关系研究是比较客观理性的,但他对中国的理解和评判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他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不能认识到美国的霸权性质、过于单方面强调美国利益等。
纵观费正清的一生,他对中国有着深刻认识,他持续观察中国,直到去世前两天,还将《中国新史》书稿交给出版社。1991年9月14日,这位国际汉学泰斗与世长辞,把自己对中国的关切之情贯穿到了人生的最后。
苏峰




 010-65363526
010-65363526 rmzk001@163.com
rmzk0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