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9年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前长达一个世纪的历史当中,中国一直处于政治混乱的漩涡当中,人民饱受内乱外辱、军阀割据、革命频发之苦。由此也就不难理解,我们从课堂上学到的中国近现代史几乎就是一部政治史。学生们知道太平天国运动,知道五四运动和毛泽东如何领导党和人民建立新中国,却很少知道这些政治事件的经济和社会背景。
学生们可能也通过课本了解到,中国农民因受到地主越加严酷的剥削而更加贫穷并因而在共产主义革命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还了解到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打破了中国本土手工业体系并且阻碍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以及1905年科举制度废止使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从此不复存在,等等。不过他们当中却很少有人能够将这些知识与中国近现代政治变迁背后的社会和经济因素建立起关联。
学生们的历史认知之所以是孤立的,原因并不在于他们的教授认为经济和社会因素不重要。其实,教授们在相关研究中已经越来越多地触及中国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固守在政治和思想领域里。正因如此,我们现在才拥有了大量关于中国近现代社会和经济历史经验的专题文献。然而,这些研究在主题方面非常分散,并且让人觉得异常深奥难懂。比如,关于江西“棚民”的研究和关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稻米价格研究等课题就非常令人感兴趣,但在课堂上讲授的涵盖上述问题的“近现代中国史”却往往令人感到不明就里。
可见,专项研究与学生在课堂上能学到的知识之间的分立使得两者正在拉开越来越远的距离。本项研究希望在运用以往研究成果中所包含的洞见基础上,对中国近现代经济和社会史做一个较为全面的呈现,从而为拉近两者之间的距离做出努力。
当一个人从事社会和经济问题研究时,他很快就会发现在其从事政治研究时所用的时间划分法不怎么好用了。比如,用后一种方法来考量鸦片战争之后近代中国的问题,即使是1793年马戛尔尼使华之后的中国问题也并无裨益;同样,清朝在1644年的建立,或者辛亥革命在1911年的爆发等重要政治事件在社会和经济问题研究中也算不上是重要的转折点。(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的成立却仿佛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和经济以及政治和历史阶段,在我看来,这是因为这场革命发生得过于晚近,以至于我们缺乏必要的历史背景去找出共产主义体系中暗含着的连续性。)
然而,即便鸦片战争不能算作“现代”中国开端的标志,中国的“现代化”步伐在19世纪60年代之后却也大大地加速了。此后,部分地,也仅仅是部分地受到西方世界的影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更多新的社会群体,这些群体逐渐从社会结构的上层开始取代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同时,秘密社团组织和土匪群体也开始活跃起来;此外,商品贸易和近代工业在中国社会中也得以发展。这些变化促使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在1860年到1949年期间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深刻变化。由此,至少从社会和经济角度来看,这九十年仿佛是一个独特的历史阶段。在这里,为方便起见,我们称这个阶段为“现代化早期”(early modern perio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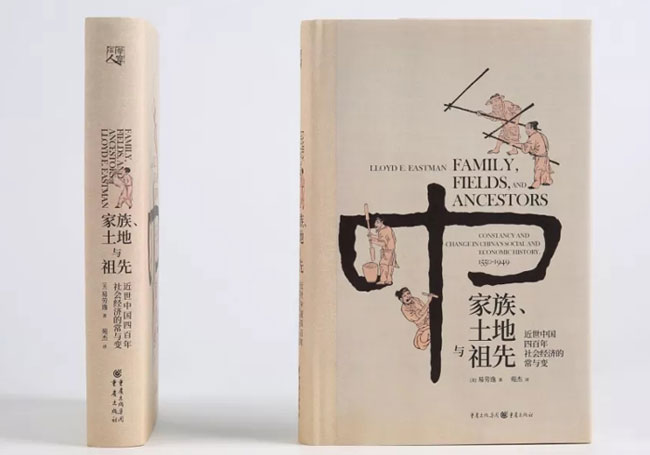 《家族、土地与祖先:近世中国四百年社会经济的常与变》 作者:[美] 易劳逸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华章同人
《家族、土地与祖先:近世中国四百年社会经济的常与变》 作者:[美] 易劳逸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华章同人
最初开始此项研究时,我并没有想从明代开始。然而,很快我就发现,对中国“现代化早期”很多社会和经济变迁问题的理解,必须先关注和探讨此前已经发生变化了的体制和结构,因此,我们有必要将视野回溯到1860年之前。可是,我们需要回溯多远呢?
有人认为应该回溯到18世纪,因为这个时期是清代发展的高峰时期,而且是传统体制依旧强健,西方影响十分薄弱的时期。然而,当我们关注18世纪并对其进行研究时,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它的确代表了清代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最高峰,而且我们更想要,也有必要再向前追溯更远,去寻找那个时代图景的社会和经济源头。因此,我在学术界以往对此研究甚少的情况下,仍旧决定从明代,特别是16世纪开始着手研究——这个时代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独特历史阶段的开端,也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中国的经济领域开启了商品化和货币化进程,对外贸易得以发展,传统社会阶层划分被打破,民众书写能力得以普及,人口得到迅速增长,这一切在接下来的两百年及更长时段里极大地改变了整个帝国的社会面貌。
当然,以往学者也同样认为16世纪在中国社会和经济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罗友枝(Evelyn S.Rawski)曾经写道:“这个时代,也就是中国帝制时代晚期(16世纪—19世纪),虽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以往任何一个时期,但其核心体制和社会经济结构方面却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对以往时期的延续。”在罗友枝之前,马若孟(Ramon H.Myers)、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等学者也有相同的发现。也就是说,我和这些学者持有共同观点,即应将1550年到1860年视为“帝制时代晚期”。
书写长达四个世纪之久的中国经济和社会史,很容易让人面临这样的风险,即可能会对特定时空中的、具有特殊性的社会和经济状况进行泛化的概括。
单从面积上讲,中国是欧洲(不算俄罗斯欧洲部分面积——译者注)的两倍,在四个世纪内,在如此广阔的国土上,社会和经济状况的差异性是相当突出的。比如,境内遍布贫瘠高地且人烟稀少的贵州在社会和生活方式等方面肯定与高度商业化且相对富庶的长江中下游省份不一样。文盲和经济窘迫的农民阶层与富裕且有文化的士大夫阶层在家庭结构、人际关系、道德观等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异。鉴此,我们如何还能对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做“一概而论”呢?
根据地域、社会和历史等方面的不同 (对社会和经济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本书的综合性质却决定它不可避免且有必要做一些一般性概括,不过我在做概括时很谨慎地标识了其适用范畴和例外情况。本书是对中国社会和经济的一项“细致而微”的研究,无法“毕其功于一役”。普遍性始终是存在的,但读者也应铭记林语堂那句话,即“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而她的民族生命,涵括了太多面向,对她难免有许许多多抵牾歧异之见解”。或许中国农民那句俗语“十里不同风”是对中国社会这种情况更为简单明了的描述。




 010-65363526
010-65363526 rmzk001@163.com
rmzk001@163.com


